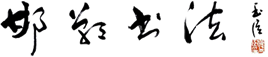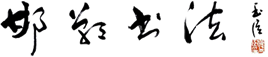寂寞不遇《韩仁铭》
翁方纲《两汉金石记》对《韩仁铭》的不遇愤愤不平:从欧阳修、赵明诚、洪适、娄机以来,皆未见之著录.《金石存》中说得更具体:此碑金哀宗正大五年出土以来,迄于明代,如都元敬、赵子凿,清代如顾亭林、顾南原等,“搜辑古碑殆遍,此碑还在京索间,绝无知之者,至刘太乙《续金石录》始载之,近乃遍粥于世矣”.如此的叙述,的确是很能证明《韩仁铭》的不幸遭际的一方成就崭然的汉碑,又是早在金代就已面世,却既不人著录也不见闻于元明清诸代专门的学者,这实在是很不可思议的。
不过《韩仁铭》最终还是得见天日.在碑侧也有金代著名书家、翰林学士赵秉文跋书.证明它也还不是最受冷落者。而在清季它为学林所重,亦即是它“遍粥于世”的时候,它也当之无愧地获得了极高评价。翁方纲《两汉金石记》又载,《韩仁铭额》属于“长短随势为之,此与《张迁碑额》皆汉隶之最得势者”。
从实际的碑额书法来看,翁方纲的评价并不过分—《韩仁铭额》的汉篆是所有的汉篆书法中最出色的一件。如果说《张迁碑额》是一种方笔缪曲的扁篆书结构的话,那么《韩仁铭额》则更具有优雅的、灵活的、自由的特征。因此作为汉篆的标准范本,《韩仁铭额》具有更大的典型性。 (来源 邯郸书法家协会:www.hdsfxh.com)
《韩仁铭额》与《张迁碑额》虽属同类,但从碑书的隶书风气来看,它却更接近于《礼器》或《史晨》的格调。杨守敬指它为“清劲秀逸,无一笔尘俗气”.这“清劲秀逸”四字.基本上已把《韩仁铭》的隶书风格概括殆尽了。细劲的笔画、优雅的波挑、典型的中锋线条与较平淡而不故为疏密的空间结构.与同时的《熹平石经》相比,它的平中见奇、静中见动的优势跃然眼前。历来评论家皆以为它是东汉隶书成熟时期的代表作,信然。
正大五年,河南荣阳令李辅之发掘得此碑,当时有赵秉文、李献能、李天翼跋语题名.有趣的是,赵秉文与李献能所持的观点针锋相对,并列于碑石左侧,令人发嚎.赵秉文认为:“韩仁,汉循吏,蚤卒,不见于史而见于此,非不幸也。”而李献能的看法完全相反:
两汉重循吏,而韩君之名不见于史,则知班、范所载,遗逸者尚多,此碑又复埋没于荒棒断垅中,阅千载而人不识,是重不幸也。
依我们看来,时隔一年的两位题名者,又同题一侧,虽是各持歧见,其实是无可无不可的。只不过以韩仁“经国以礼,刑政得中”,政绩斐然.。一逢早夭而蒙郡遣吏以少牢祠之,本来是足以青史.留名,却被人遗忘久之。想来总觉得有所欠缺。李献能早在金时即以碑石埋没与人名遗逸作比,已是感叹良多。而再经元明清的屡见遗于诸家著录,一如此寂寞,则不识之论,几近乎谶语矣。
不过,反面的谶语也还是有:赵秉文跋有云:“自古贤达,埋光铲采,堙灭无闻,亦何可胜数,抑有时而不幸也。后千百岁,陵谷变易,独此碑尚存,李侯(辅之)之名,托此以不朽,亦未可知也。”这似乎也预示着清季《韩仁铭》的重新复出早在算计一之中。论人之幸与不幸,两人相对各持一端,论碑一版遇与不遇,又是各有歧见互不相让,甚至连偶然的“谶语”,也还是南辕北辙,同处一时又同题一碑,这赵秉文与李献能,真是可爱的一对又是难得的一对。吁!
关连: 书法 曹真残碑 上尊号奏 尹宙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