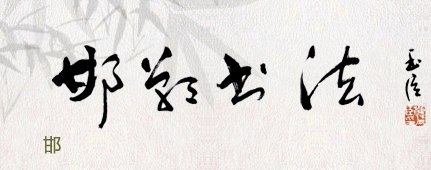详细内容
前赤壁赋—“坡公之兰亭也”
《前赤壁赋》—“坡公之兰亭也”
少焉,月出于东山之上,徘徊于斗牛之间。白露横江,水光接天。
纵一苇之所如,凌万顷之茫然。浩浩乎如凭虚御风,而不知其所止,飘
飘乎如遗世独立,羽化而登仙。
纵一苇之所如,凌万顷之茫然。浩浩乎如凭虚御风,而不知其所止,飘
飘乎如遗世独立,羽化而登仙。
这一种宽阔博大的襟怀,古往今来,曾经感动了多少人?而且,这是怎样的一种驾驭文字描景抒情的卓绝能力啊!前后《赤壁赋》被传为古代散文名篇,虽有赋体的形式,却更有充沛的激情与高旷的格调,全无雕琢刻意之迹。诚可以上攀屈骚庄辞,谓为文学史上的一块丰碑。于是,就有了董其昌的跋文:
东坡先生此赋楚骚之一变,此书兰亭之一变也。宋人文字俱以此为
极则。
极则。
所谓的宋人文字,并不只指文章:“字”应该是指书法,于是才有理由说是“俱”如此—“俱”如此是至少在两项之上,仅一项是俱不起来的。这样董其昌的观点就十分鲜明了:无论是文章还是书法,苏东坡的《前赤壁赋》均是宋代第一。
是否真的第一,当然也是无法证实的空话。不过苏轼此卷是珠联璧合:文章既是绝世名作。书法也是一代风范,因此在历史上的确被推为典范之作—是苏东坡书风的精华所在。董其昌并有指此书为“坡公之兰亭也”。若论抒情性格,则《黄州寒食诗卷》或未逞多让,但东坡随手写去的小行书手札尺9不少,正规的楷法却很少见到,《前赤壁赋》却是用功甚勤的楷书。我想,既是自家得意文章,作书时自然不肯苟且随意以免以书害辞.用小楷书作工稳体,应该表明苏东坡于此是十分切切在意的。作为一个间接的证据,则清吴承泽《庚子消夏记》还有一评:
是否真的第一,当然也是无法证实的空话。不过苏轼此卷是珠联璧合:文章既是绝世名作。书法也是一代风范,因此在历史上的确被推为典范之作—是苏东坡书风的精华所在。董其昌并有指此书为“坡公之兰亭也”。若论抒情性格,则《黄州寒食诗卷》或未逞多让,但东坡随手写去的小行书手札尺9不少,正规的楷法却很少见到,《前赤壁赋》却是用功甚勤的楷书。我想,既是自家得意文章,作书时自然不肯苟且随意以免以书害辞.用小楷书作工稳体,应该表明苏东坡于此是十分切切在意的。作为一个间接的证据,则清吴承泽《庚子消夏记》还有一评:
《赤壁赋》为东坡得意之作,故屡书之,此本小字楷书,尤有精彩。
吴承泽看到的一定不止一本。这样,一是“屡书”所体现出来的自鸣得意情绪,二是此本的“小字楷书”表现出来的认真用功,这些都可以证明,苏东坡的书写《赤壁赋》绝非是一个随便玩玩的过程.当然随之而来的结果也十分明显——所谓的“坡公之兰亭也”,一是指书法,二也是指《赤壁赋》文章典雅自然有如《兰亭序》,这都是文学史上的一代名作,是后人很难随意忘却的。
董其昌对《赤壁赋》的又一激赏,则是在它的墨法。当然,苏东坡喜用浓墨,且还自己研制墨锭,据说还弄得灰头土脸。董其昌在王履吉家看到原作云:
董其昌对《赤壁赋》的又一激赏,则是在它的墨法。当然,苏东坡喜用浓墨,且还自己研制墨锭,据说还弄得灰头土脸。董其昌在王履吉家看到原作云:
每波画尽处,每每有聚墨痕,如黍米珠,恨非石刻所能传耳。差乎, 世人且不知有笔法,况墨法乎?
平面的纸上竟能出现鼓凸如黍米珠的墨痕,这真让人瞳目结舌。董其昌认为此是体现出一种“法”的存在;依我想来,作为普遍的法未必有实际意义,但据以理解东坡的笔力却是十分有价值的。此语出自好用淡墨的董其昌之口,则更具有说服力。
苏子在赤壁舟中是“肴核既尽,杯盘狼藉,相与枕藉乎舟中,不知东方之既白”,似乎颇有勘破世尘,意在知与不知之间,那么我们对《前赤壁赋》持什么态度呢?也是洒脱如此,知或不知,均已被化人茫茫虚白,已经无关宏旨了?
苏子在赤壁舟中是“肴核既尽,杯盘狼藉,相与枕藉乎舟中,不知东方之既白”,似乎颇有勘破世尘,意在知与不知之间,那么我们对《前赤壁赋》持什么态度呢?也是洒脱如此,知或不知,均已被化人茫茫虚白,已经无关宏旨了?
十届国展广西展区
(编辑:无名)
上一篇:朱曼妻薛买地宅券—有趣的疑问 下一篇:苏轼柳州罗池庙碑的山野之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