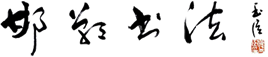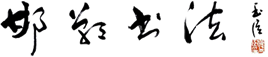最早的有纪年写经—西晋《诸佛要集经》
经卷书的兴起,应当归功于中国的佛教大盛。虽然我们不能忘记周武宗、唐武宗的灭佛运动,释道相争也是宗教史上的老话题,但似乎这外来的佛教却总有强有力的生命力,以客教的不利地位却能顽强不懈地渗透到中国民众中来,在社会生活、民俗、文化诸方面表现出无所不在的影响。
经卷书的存在从西晋开始一直沿袭到唐末北宋,在一个地域的限制下,却也有持续上千年的历史进程。这是尤为令人赞叹不已的。此外,以书法家的立场去加以排比,则我们无妨把自楚帛书、楚简秦简作为墨书的第一站,把汉竹木简牍与帛书作为第二站,则自西晋以下的经书则可作为第三站,直可持续到唐末。第一站是战国时期,第二站是汉,第三站是自魏晋到唐宋。当然,如再往前伸延,则如墨书陶片“祀”,也可算是更早的一站。这样,历史又可上推殷商或西周的甲骨文、青铜器的早期时代。
这为我们带来了两个有价值的启示。第一是这一个系列的成形有相当的价值—墨迹史书写史的价值。把它与同时的石刻或钟鼎甲骨系列相比,则后者正统而前者属草民所为。因此,书法史注重后者的传统而忽略前者的传统价值。但事实上,作为传统,墨迹手书这一系丝毫也不逊于石刻这一系,问题只是后人没有主动去选择它而已。阮元的《南帖北碑论》只是瞄准六朝以后,其实如上溯殷周,他或许更会感到惊喜的。第二是一旦这个系列成立,则再往宋以下的尺犊小**L,中堂大轴又都是墨书的天下,石刻却慢慢被推下历史舞台。于是石刻或锲刻铸造的一系只是从商末到唐宋,占据历史的中间一段一当然这是最重要的一段。而墨书却能贯穿整个书法史或书写史,从商末的墨书陶片“祀’字,到楚帛书、楚简秦简,到汉竹木简、汉帛书,到魏晋写经书。当然还有二王以下,到了唐代也还有无数的墨书,宋以后,则干脆是墨书的天下了.以这样一个系统的立场整理出墨书的书法史,未知诸君以为何如?
这当然也还是比较简单的处理方法。因为事实上书法不仅仅是刻锲与墨书的区别,比如应用场合的正规与草率、应用或制作的人的身份的尊卑贵贱,都对书法史有相当大的影响.不过我仍然愿意有此一项假设,因为很明显,这样的假设符合书史研究多元化的学术立场。
以这样的立场去看晋人写经《诸佛要集经》,我们就不会为它的平淡而失望,因为它同样具有墨书一系的史的实证功能。《诸佛要集经》书于西晋惠帝元康六年(296),是迄今为止最古的有纪年的经书—因为它有纪年,又是年代最早的.在众多的无名无纪年的经书群中显然鹤立鸡群有着突出的价值,不但对于整个敦煌石室经书的断代提供了宝贵的证据。就是在书体、书风方面,也为西晋书法的大致风貌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典范。比如将《诸佛要集经》与同时的陆机《平复帖》的书风相比,再参以正规与草率、文人与写经手的差别,不知诸公当有何想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