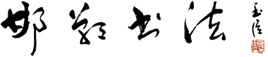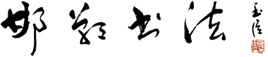吴宽《诗稿》中的苏轼格调
吴宽曾为李应祯作有《太仆寺少卿李公墓碑铭》,他们又都是南京长洲人。既谊为挚友,又是同乡同好,应该互有影响。特别是弘治中,吴宽为吏部右侍郎,旋摆礼部尚书,与官太仆少卿的李应祯为一殿之臣,谈书论艺,颇为款洽,则他们之间更有可能取长补短了。但是很有趣,吴宽的书风却截然不同于李应祯—李书尖锐刚折,吴书却宽博厚重,李书浇薄有明时习气,吴书却骏骏欲度元人之前,几与宋贤并驾齐驱了。
明人书风的一大转折是从晋唐的范围急剧转向宋人。沈周、文微明的学习黄山谷是有目共睹的事实。而吴宽,则是学苏轼的代表书家。
学苏必致肥厚,肥厚者点画浑圆而粗壮之谓也。黄山谷讥苏东坡的“石压蛤蟆”,实在是最形象的比喻。吴宽学苏倘一味取苏之丰润月巴厚,失其精气所在,则疲软弊必随之而生。历来学苏难有大成,也多是在这一关键上有些须失误。吴宽学苏的不利面是他只能面对苏轼的遗作,从形貌上去推敲把握原帖的点画技巧,但有利一面则是他本人也是满腹珠矶,而更重要的还在于他生逢明代,从明初三宋到董其昌,皆注重清雅飘逸之气但时见峭薄之态。这峭薄之态在李应祯辈是时势所压,在董其昌辈则是趣味使然,要之皆很难以此上追唐宋的时代气息。但时代之失却有可能成为吴宽的个人之得。在面对苏轼的丰厚胶妍之时,能渗入一丝峭薄之气,则柔而未必无骨,润而未必失锐。钩连点画间,仍然饶有顿挫剔挑的节律。因此,峭薄对于学黄的沈周、文微明,学米的董其昌是一大致命伤,使他们永远只 能局促辕下,难成大气候,也难有大风采,但对于吴声却是个意想不到的收获。事实上,他本人未必意识到,只不过是置身于明代中叶这一环境中,出手即有峭薄的本能,以之学苏轼,反倒显得骨力洞达、爽爽风姿。同时人王鳌《震泽集》有评:“宽作书姿润中时出奇崛,虽规模于苏,而多所自得。”在此中,姿润可指苏书原有的丰腆之美而言,则奇崛可指吴宽本人的峭薄而言。
当然,这种以峭薄济肥厚的立场是有节制的。把苏东坡书法写得浊重可厌自不算高手,但若随心所欲,把苏字写得尖刻可畏或桃挞过甚,也同样难人时人之眼。吴宽于此掌握得恰到好处。他对风格的界定有自己的心得,绝不因峭薄而有碍苏字风格的纯正。《诗稿》既见锋锐,又不失圆润之旨,比起文、沈的学黄.在化入己意方面自然强胜多多。于是我们在王鉴的评价之外又可看到一条相对应的评价。 (来源 邯郸书法家协会:www.hdsfxh.com)评价出自同时书家邢侗之手:“匏翁书法法苏学士,浓颜厚面,祛去吴习。亦毕竟赵宋本色耳,超著实难。”这被吴宽“祛”去的“吴习”,即是我们所说的吴门书家常有的峭薄习气。峭薄者气必不厚,向为宋前书家所未取,明时时势使然,书家只取轻捷流畅为正,体势愈见单薄。吴宽能有见及此,虽未必是开宗立派的大家手笔,但却不失为扛鼎巨手.严格说来,他的成功因为逆时流之所向,因此更难能可贵。后人只看文、沈,忽视他的价值,实在是很不应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