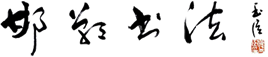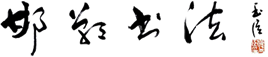漫漶的“囤碑”—《禅国山碑》
宋欧阳修《集古录》有云:“孙皓天册元年,禅于国山,改元天玺,因记其所获瑞物、刊石于山阴。”国山今在江苏宜兴。据《宜兴志》载,国山原名离墨山,在宜兴张清镇北十里。
三国时篆书碑甚少,曹魏身处中原,以东汉隶书为主要书风,西蜀书法传世太少,难见典型。而孙吴江南一隅,竟连续出现《天发神谶碑》和《禅国山碑》,均为篆书,颇令人感到其中有些奥妙。是当时孙吴尚处化外,还保留篆书遗风,还是孙吴不奉曹魏正朔,有意上取篆书以为区别?郑重其事的《上尊号奏》与《受禅表》,相对于同样郑重其事的《禅国山碑》《天发神谶碑》,其间的书体差距,我总觉得应该有一些微妙的含义在。若不然,孙吴的第一代孙坚或孙策也自称是汉室之臣,在汉隶已风行数百年之久的当时,硬要跨越这一时期,平白无故地去上追什么古风,怎么想也是件大怪事。
《禅国山碑》能否成为地道的吴越书风的代表,甚难评定。三国魏、蜀、吴的国作均短,除了魏是上承两汉下开西晋,因此在书风上较有规律可按,是典型的传统隶书与新兴楷书之间的统系之外,蜀、吴书风因存世太少,是否有一个固定的风格型存在也还难说。后世评论家如杨守敬《平碑记》对它的看法,并非是因为它属于“代表作”,而是由于硕果仅存,难能可贵,故加以特殊关照罢了,请看他的自述:
秦汉篆书自《琅邪台》《禽山石阔》数碑而外罕有存者,唯此巍然
无恙,虽漫漶之余,尚存数百字,玩其笔法,即未必追踪秦相,亦断非
后代所及。
可见,他着眼的是《禅国山碑》的“巍然无恙”,是退而求其次的口吻。至于后面的称颂,其实也只不过是清代博古家的惯用伎俩。《禅国山碑》尚存的数百字,无论是结构还是更重要的“笔法”,早就已被漫法弄得面目全非.既难细细“玩”来,更逞论“追踪秦相”等等的泛泛之誉了。所谓的后代所不及,完全是出于好古崇古的“学究”心理。
不过,后世临习此碑者也大有人在。从博古式的学究态度到艺术家以独特眼光发掘这漫德之美,其间所包含的立场转移,主要表现在于:艺术家是以主体的选择去主动发掘、发现这种残破的、迷蒙的、苍茫的历史美。对于丫个富于创造力的艺术家而言,越含糊的对象给主体提供的驰骋想象余地、促使他调动自身的艺术能力加以补充的机会也越大。因此,忠实的一丝不苟的临摹者对于《禅国山碑》这样的对象可能束手无策,但一个有活力的艺术家,却可以将自己的追求与《禅国山碑》这样的可供再造想象的欣赏对象作有机化合,从而摸索出一些新的风格之路来。
《禅国山碑》书法的漫S.,以及由此而来所获的质朴、浑厚等等评价,据说还得之于碑形本身。此碑石形微圆,四面环刻,宋赵彦卫《云麓漫抄》称:乡人又俗呼此碑为“囤碑”,“议其石圆八出形如米廪云”,如此说来,则浑圆而不见锋芒的线条,更应是基于石形本身的刻刊条件,而与人为的“笔法”未可牵强凑合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