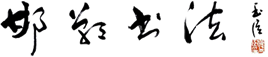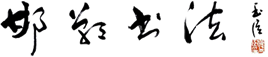徐渭—书法史上的梵高
徐青藤是个地道的狂人.张旭式的“以头濡墨”和米带式的“反系袍袖,固然是书法史上有名的逸事,但与徐渭相比,不过是担了个虚名。据查,徐渭的疯狂不仅仅出于艺术行为,他好像真的有点精神病式的疯。病理的疯一旦转化为艺术行为的狂,其激烈程度可想而知。我们不禁想起了西方绘画史上的梵高,他们堪可配成一对。
疯子永远也成不了艺术家,但徐渭却成功了。他的水墨葡萄在绘画史上有突出的地位;他的《四声猿》也是文学史上不可忽略的一笔。那么他的书法如何?在明代书风略嫌沉闷的环境对照下,他似乎是呼啸而起,以彻底的狂态为书法史施加为书法史施加了浓重的一笔。文微明、赵松雪或是董其昌自然远避唯恐不及,即是才子如祝枝山,乃至上溯宋代苏、黄、米,在气势上也不得不逊他一席之地。书法当然不只是气势问题,但以他的如此胆魄作如此狂书,卒至取得如此大影响,我以为并非偶然。元明时代对二王的回归与继承,使理性主义占了上风,动必有则,愈演愈烈,故而赢弱积深,徐渭的反叛,也许可以算是对理性主义末流的一种清算吧?
强劲粗犷的线条,舞蛇走地。驰纵跳腾:间架完全被打散.服从于更整体的章法效果,字的可识性显而易见地受到了削弱:而且提按顿挫的笔法也被更含混,更博大的审美意识所取代。局部的技巧美忽然丧失了原有的价值。一切取决于视觉整体感,这就是徐渭的反叛内容。在书法史上还很难找出这么一个典型,无论是二王,还是颜柳苏米等,即使是张旭、怀素,在徐渭的气势面前也不得不慑眼。当然,缺陷也显而易见:注重整体的同时带来技巧的不够精到,时出败笔,而且创作的成功率极低。精者可谓惊天地动鬼神,粗劣之作则如村夫态。在徐渭传世作品中,精者甚少而粗者却屡见不鲜,这也正是明代人趋仿古人时的共性现象。
但徐渭还是震烁古今的。他的非理性表现为我们留下了关于明代书法、整个书法史上的一连串有深度的命题。如果没有他,我们很难想象沉滞的明代书坛还有些什么值得自傲的所在;如果没有他,我们也无法想象出明末表现主义思潮在书法史上是如何崛起,使整个书法史在沉寂后猛然一震;如果没有他,书法史上的表现主义思潮永远也找不到一个定位的落点—没有一种思潮或思想可以不落实到具体的人物或创作上来。当然还有:如果没有他,我们对明末王铎、傅山竟会有如此狂放但却又是如此理性的现象必然会百思不得其解。但有了徐渭,一切都可以解释了:因为有他的狂放,所以书法史对疯狂与奔走呼号不再持一种突兀感和排斥态度,相反一些书法家还从徐渭身上找到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。比如取其狂放但舍其芜乱,而济之以严整;取其厚劲但舍其粗糙,而济之以沉实。当然从总体上说,则在徐渭冲决了理性的法规之后,后人又面临着高一转次的重新构建,正是在这破与立的不断循环中,构成了一部浩瀚伟大的书法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