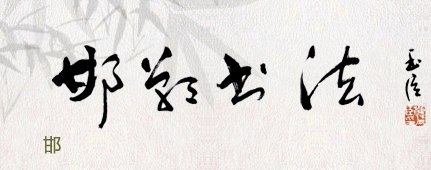详细内容
薛元明感觉褚遂良
薛元明:感觉褚遂良
魏晋至隋唐时期,楷书逐渐消尽了隶书古意,拙扑粗野转化为典雅精美,隋代的《董美人墓志》和《龙藏寺碑》和初唐楷书风格已经十分接近。褚遂良因为能写王书而受到唐太宗的青睐,举为重臣,实质上,褚遂良在唐朝的政治生涯中,发挥了很大作用,“两朝开济老臣心”,一生竭智尽忠。初唐楷书肇始“尚法”端倪,褚遂良更是功不可没,之所以这样说,因为褚遂良楷书和以往时代划上休止符,是“唐楷第一人”。初唐欧虞褚三家虽皆承六朝遗风,兼南北意蕴,融合不同风格,但有明显差别。欧虞入唐已是暮年,虽有二王遗风,但更多北碑方正一路的影子,欧阳询表现的尤其充分和明显,清雅秀丽中包含雄强之气。虞世南书法较之二王风流潇洒显得沉稳蕴籍,收敛了风流华彩,李煜说:“虞世南得右军之美韵,而失之俊迈”。对于褚楷则有很高的评价。《唐人书评》“褚遂良书,字里金生,行间玉润,法则温雅,美丽多方”。张怀瓘《书断》说:“褚遂良善书,真书甚得媚趣,若美人婵娟,似不任乎罗绮,增华绰约,甚有余态,欧虞谢之。”
褚遂良书法作品数量超过其他初唐书家,但其中有很多伪托之作,如行书《枯树赋》、《唐太宗哀册》以及《倪宽瓒》等。他的书法风格明显地分为学碑和学王二个时期。学碑期宗欧虞,受北碑书风影响,代表作有《伊阙佛龛碑》,此碑书于唐贞观十五年(公元641 年),时年46岁。用笔工整,以方笔为主,结字方正平稳,以端庄取胜,极合法度,点画棱角分明,横画两头偏粗中间细瘦,略带波势,平正中见遒劲,捺笔一波三折,既有外拓之险劲,亦有内敛之含蓄,整体具浓厚的隶书笔意,揖让处理受汉隶《礼器》影响极大。苏轼《东坡集》中道出“褚河南书,清远潇散,微杂隶体。”刘熙载认为“兼有欧虞之胜”,集两家之长。康有为虽讥讽唐楷“状如算子”、“截鹤续凫”,却称赞该碑“清虚高简”。但相比褚氏后期作品的随意和轻松自然,还有很多刻意之处,笔法方面也缺少灵动的变化。
褚氏这一时期代表作除《伊阙佛龛碑》外,还有《孟法师碑》,书写时间稍晚一年,仍然不能摆脱欧虞的影响,用笔接近欧阳询,结字则有虞世南的影子,但变法已见端倪。行笔间有了起伏和较强的节奏韵律感,较之《伊阙佛龛碑》更为圆润秀媚,字型左紧右舒,相互间呼应更为明显,结构端庄大方,疏密、巧拙呈现出不同变化,一些呆板的成分消失了。如果就褚遂良一生书法发展来作总的评价,还是缺少个人面目,因为楷书风格塑造较行草书更难。
大字《阴符经》书写时间和《伊阙佛龛碑》大体相同或略早,在落款中有“起居郎”字样,褚遂良任起居郎在贞观10年,即636年,因而有此一说。《阴符经》笔势更加强烈,笔画间连绵牵丝呼应比比皆是。朱和羹《临池心解》说:“褚登善《阴符经》参以《急就》,以楷法行之,遂为千古绝作,其后无闻焉。”对照《阴符经》和《伊阙佛龛碑》,有很明显的差别,故有论者言《阴符经》的真实性要大打折扣。但伪作非劣作,米芾生前就极为推崇该帖,引以为范,受益匪浅。笔者认为,最重要的是《阴符经》可以体现出褚遂良的艺术水平,抑或是同时代学褚高手的模仿之作。《阴符经》除大字外,尚有小楷和草书两体,都是伪托之作。
最可信而又最能代表褚遂良水平的乃学王时期的代表作《雁塔圣教序》,作于653年,褚遂良时年58岁,已入暮年。原碑共有两块,在陕西省西安市大雁塔底层南墙,左右各一,至今保存完好。和学碑时期有明显变化,用笔藏锋逆入,一丝不苟,方圆兼施,笔画肥瘦互见,流利飞动,取弧势以增强笔力,参以二王行书笔法增加华美意蕴,相互间的动势呼应更加强烈,有意识地强调线条的曲线美和韵律美,风姿绰约动人。梁巘《评书帖》说:“褚书提笔空,运笔灵,瘦硬清挺,自是绝品。”结字中宫敛紧,疏密有致,字形宽绰,四周舒展,章法完全是汉隶格式,字间大于行间,气韵直逼钟王,而显褚家清逸。米友仁《跋〈雁塔圣教序〉》中说:“褚书在唐贤名士中为秀颖,得王羲之之法最多者。真字有隶法,自成一家,非诸人可比肩。” 可以说,《雁塔圣教序》是褚遂良个人书风确立的标志,用笔和结字都丰富多样,从方整向多种形式变化,融入二王笔意,摆脱欧虞面目,形成自我。当代书家潘伯鹰、徐无闻和沈觐寿等都是善褚书高手,皆以《雁塔圣教序》为范,足见影响之深。
褚遂良书法在唐代就产生了巨大影响。张怀瓘说:“薛稷书学褚公,尤尚绮丽媚好,肤肉得师之半矣,可谓河南之高足,甚为时所珍尚。”朱景玄《唐朝名画录》中称“薛稷学书师褚河南,时称‘买褚得薛,不失其节。’”对照薛稷书迹,虽名立列“初唐四家”,实际逊色。薛稷虽得其势,但失却了变化的随意和谐。薛稷从弟薛曜更胜一筹,对褚书不作亦步亦趋的模仿,而是加以发挥,有所创造。
薛稷兄弟之后,同年出生的张旭和李邕,则是褚遂良书风转变为颜真卿书风的过渡人物。唐代楷书也从初唐向盛唐逐步转型。张旭虽为一代草圣,但楷书功底惊人,风貌清虚简淡,仍然是初唐书风,受褚遂良影响很大。李邕楷书却大有改观。和褚遂良楷书一样,都为行楷。褚书中更多的保留了二王行书笔意和隶书痕迹,李邕不象褚遂良注重用笔的华丽巧饰,体现出碑格,笔画厚实,古拙刚硬,不乏婉转流畅,天趣自然,以“左低右高、上舒下敛”的结构变革二王行草,峻拔开张、稳固结实而气宇喧昂。李邕成熟期书法形态中很难找到二王的影子,用笔刚健,笔力雄强,无牵丝映带的虚笔连绕。通过横画欹斜来取势,这是李褚二人的共同点,但和褚书字形长宽扁高变化多相比,李邕字形变化要少一些,基本上忠实于二王体格。
颜真卿是唐代除薛稷外受褚遂良影响最大的书家。刘熙载《艺概•书概》中“褚河南之书为唐之广大教化主,颜平原得其筋”,从颜成熟期作品字形上来看,二者悬殊很大,实质上同声相息,颜从褚中化出,胜过薛稷仅得皮毛。颜字字形的宽博,捺画一波三折运笔,取法着意篆隶方面,都是受褚的启发。依笔者愚见,唐代精神暗合二王惟有褚颜二人。只是颜真卿将褚遂良的清逸变为沉雄,笔画细腻变成粗壮丰满,横画的欹侧变成从“平直到平直”,以正面示人,空间分割极为均匀,最大限度地发挥线条的张力作用,突破二王藩篱,洗尽贵族脂粉,以雄浑博大、黄钟大吕的盛唐之音取代了初唐潇洒飘逸的丰姿。在变法上,颜真卿比李邕更彻底。
宋代对褚理解最深的要数米芾,他在《续书评》中说“褚遂良如熟驭战马,举从动人,而别有一种娇色。”并且在《自叙帖》中说“余初学颜七八岁也,……乃慕褚而学最久。”米芾性格癫狂,自视甚高,在书学观念方面是离经叛道之人,籍助癫狂之口说出很多骇人听闻之语,诸如“一扫二王恶迹,照耀皇宋万古!”,“欧虞古法亡矣”,“颜书真入俗品”之类的话。但留心米芾言论,一生从未对褚遂良有半点微词。以米芾狂妄的为人,是不会轻易佩服一个人的,除非正对自己胃口。米芾对大字《阴符经》极为称道膺服,其行书用笔灵动多变,锋出八面,爽利有力,不能不归结于褚氏启发。
褚遂良一生书迹皆为行楷,因为他不愿耽于笔墨纸砚苦役劳顿,做个书工。他的成就可概括为两点,一是个人永无满足,不断探索,褚遂良实际上是由隋至唐楷书演绎的缩影,他一生墨迹的变化见证了这一点;二是他既能吸收前人精华,也能把握时代潮流,做到 “古不乖时,今不同弊”。褚遂良在习王浪潮下不能置身事外而另僻蹊径、独张一军,他的过人之处在于把握了书风变革的历史潮流,是二王体系中的得力干将,既实践了崇王理想
感觉褚遂良
薛元明
唐代楷书是后人无法企及的高峰,经历了初唐的奠定基础,颜真卿的集大成和柳公权的法度精整化等三个阶段。而初唐肇始“尚法”端倪,褚遂良功不可没,之所以这样说,因为褚遂良楷书和以往时代划上休止符,是唐楷第一人。在初唐欧、虞、褚三家书法中,虽皆承六朝遗风,融合南北不同风格,兼南北意蕴,但有明显差别。欧、虞入唐已是暮年,有“二王”基因,但更多北碑方正一路的影子,欧阳询表现的尤其充分和明显,清雅秀丽中包含雄强之气。虞世南书法较之“二王”风流潇洒而显得沉稳蕴藉,收敛了一些风流华彩。李煜说:“虞世南得右军之美韵,而失之俊迈。”而于褚遂良楷,则有很高的评价。《唐人书评》“褚遂良书,字里金生,行间玉润,法则温雅,美丽大方”。张怀 《书断》说:“褚遂良善书,真书甚得媚趣,若美人婵娟,似不任乎罗绮,增华绰约,甚有余态,欧、虞谢之。”
褚遂良书法风格明显地分为学碑和学王二个时期。学碑期宗欧、虞,受北碑书风影响,代表作有《伊阙佛龛碑》,此碑书于唐贞观十五年(公元641年),用笔工整,以方笔为主,结字方正平稳,以端庄取胜,极合法度,点画棱角分明,横画两头偏粗中间细瘦,略带波势,平正中见遒劲,捺笔一波三折,既有外拓之险劲,亦有内敛之含蓄,整体具浓厚的隶书笔意,揖让处理受汉隶《礼器碑》影响极大。苏轼《东坡集》中道出“褚河南书,清远萧散,微杂隶体”。这一时期代表作除《伊阙佛龛碑》外,还有《孟法师碑》,书写时间稍晚一些,变法已见端倪。行笔间有了起伏和较强的节奏韵律感,较之《伊阙佛龛碑》更为圆润秀媚,字型也开始有变化,左紧右舒。
学王时期主要代表作有《圣教序》,和前一时期又有明显变化,用笔藏锋逆入,一丝不苟,方圆兼施,笔画肥瘦互见,流利飞动,取弧势以增强笔力,参以“二王”行书笔法增加华美意蕴,相互间的动势呼应更加强烈,有意识地强调线条的曲线美和韵律美,风姿绰约动人。梁山献《评书帖》说:“褚书提笔空,运笔灵,瘦硬清挺,自是绝品。”结字中宫敛紧,疏密有致,字形宽绰,四周舒展,章法完全是汉隶格式,字间大于行间,气韵直逼钟王,而显褚家清逸。米友仁《跋雁塔圣教序》中说:“褚书在唐贤名士中为秀颖,得王羲之之法最多者。真字有隶法,自成一家,非诸人可比肩。”暮年之作《阴符经》笔势更加强烈,笔画间连绵牵丝呼应比比皆是。朱和羹《临池心解》说“褚登善《阴符经》参以《急就》,以楷法行之,遂为千古绝作,其后无闻焉。”
褚遂良书法在唐代就产生了巨大影响。薛稷是首位学褚遂良楷书之人。张怀 说:“薛稷书学褚公,尤尚绮丽媚好,肤肉得师之半矣,可谓河南之高足,甚为时所珍尚。”朱景玄《唐朝名画录》中称“薛稷学书师褚河南,时称‘买褚得薛,不失其节’”。对照薛稷书迹,虽名立为“初唐四家”,实际逊色。除薛稷外,唐代受褚遂良影响最大的当数颜真卿。刘熙载《艺概·书概》中说:“褚河南之书为唐之广大教化主,颜平原得其筋,徐季海之流得其肉。”从颜成熟期作品字形上来看,二者有很大悬殊,实质上精神暗合,胜过薛稷的单纯地走形式之路。颜字从字形的宽博,捺画的一波三折运笔,取法着意篆隶方面,都是受褚的启发,是从褚中化出的。依笔者愚见,唐代直通“二王”惟有褚颜二人。只是颜真卿将褚遂良的清逸变为沉雄,笔画细腻变成粗壮丰满,横画的奇支侧变成从“平直到平直”,以正面示人,空间分割极为均匀,最大限度地发挥线条的张力作用,突破“二王”的藩篱,洗尽贵族脂粉,以雄浑博大、黄钟大吕的盛唐之音取代了初唐潇洒飘逸的丰姿。
宋代对褚理解最深的要数米芾,他在《续书评》中说:“褚遂良知熟驭战马,举从动人,而别有一种娇色。”并且在《自叙帖》中说:“余初学颜七八岁也……乃慕褚而学最久。”米芾性格癫狂,自视甚高,在书学观念方面是离经叛道之人,藉助癫狂之口说出很多骇人听闻之语,诸如“一扫‘二王’恶迹,照耀皇宋万古”,“欧虞古法亡矣”,“颜书真入俗品”之类的话。但任何书家都是血肉丰满的,如果就这些来判定,不过是皮相之论。虽有偏颇,但是一家之言。留心米芾言论,一生从未对褚遂良有半点微词,以米芾狂妄的为人,是不会轻易佩服一个人的,除非正对自己的胃口。米芾对大字《阴符经》极为称道服膺,其行书用笔的灵动多变,锋从八面,爽利而有力,不能不归结于褚氏的启发。
褚遂良行书的隶意更多地保留在字形中,从这一点上来说,比起大王化为无形要略逊一筹,但正是这字形中的隶意,也就使后学者有了探寻的罅隙。褚遂良在习王浪潮下不能置身事外而另僻蹊径、独张一军,他的过人之处在于把握了书风变革的历史潮流,是“二王”体系中的一位得力干将,既实践了崇王理想,也构建了盛唐的法度,彻底完成了从尚韵到尚法书风的转变。朱长文《墨池篇》说:“遂良书多法,或学钟公之体,而古雅绝俗;或师逸少之法,而瘦硬有余。至于章草之间,婉美华丽,皆妙品之尤者也。”综观唐楷,欧、虞为北朝遗风,薛稷学褚而无个人面目,颜虽集大成,失之粗鲁,柳公权专尚清劲,但骨节嶙峋,寒俭之气时生,惟独褚遂良书浑厚华滋、丰姿绰约。“是褚遂良的字让人懂得什么是节奏,什么是书写的快感,什么叫得心应手。”(章祖安语)褚遂良对唐代书法乃至整个书法史来说,都是不可忽视的。
感觉褚遂良
■薛元明
魏晋至隋唐时期,楷书逐渐消尽了隶书古意,拙扑粗野转化为典雅精美,隋代的《董美人墓志》和《龙藏寺碑》和初唐楷书风格已经十分接近。褚遂良因为能写王书而受到唐太宗的青睐,举为重臣,实质上,褚遂良在唐朝的政治生涯中,发挥了很大作用,“两朝开济老臣心”,一生竭智尽忠。初唐楷书肇始“尚法”端倪,褚遂良更是功不可没,之所以这样说,因为褚遂良楷书和以往时代划上休止符,是“唐楷第一人”。初唐欧虞褚三家虽皆承六朝遗风,兼南北意蕴,融合不同风格,但有明显差别。欧虞入唐已是暮年,虽有二王遗风,但更多北碑方正一路的影子,欧阳询表现的尤其充分和明显,清雅秀丽中包含雄强之气。虞世南书法较之二王风流潇洒显得沉稳蕴籍,收敛了风流华彩,李煜说:“虞世南得右军之美韵,而失之俊迈”。对于褚楷则有很高的评价。《唐人书评》“褚遂良书,字里金生,行间玉润,法则温雅,美丽多方”。张怀瓘《书断》说:“褚遂良善书,真书甚得媚趣,若美人婵娟,似不任乎罗绮,增华绰约,甚有余态,欧虞谢之。”
褚遂良书法作品数量超过其他初唐书家,但其中有很多伪托之作,如行书《枯树赋》、《唐太宗哀册》以及《倪宽瓒》等。他的书法风格明显地分为学碑和学王二个时期。学碑期宗欧虞,受北碑书风影响,代表作有《伊阙佛龛碑》,此碑书于唐贞观十五年(公元641 年),时年46岁。用笔工整,以方笔为主,结字方正平稳,以端庄取胜,极合法度,点画棱角分明,横画两头偏粗中间细瘦,略带波势,平正中见遒劲,捺笔一波三折,既有外拓之险劲,亦有内敛之含蓄,整体具浓厚的隶书笔意,揖让处理受汉隶《礼器》影响极大。苏轼《东坡集》中道出“褚河南书,清远潇散,微杂隶体。”刘熙载认为“兼有欧虞之胜”,集两家之长。康有为虽讥讽唐楷“状如算子”、“截鹤续凫”,却称赞该碑“清虚高简”。但相比褚氏后期作品的随意和轻松自然,还有很多刻意之处,笔法方面也缺少灵动的变化。
褚氏这一时期代表作除《伊阙佛龛碑》外,还有《孟法师碑》,书写时间稍晚一年,仍然不能摆脱欧虞的影响,用笔接近欧阳询,结字则有虞世南的影子,但变法已见端倪。行笔间有了起伏和较强的节奏韵律感,较之《伊阙佛龛碑》更为圆润秀媚,字型左紧右舒,相互间呼应更为明显,结构端庄大方,疏密、巧拙呈现出不同变化,一些呆板的成分消失了。如果就褚遂良一生书法发展来作总的评价,还是缺少个人面目,因为楷书风格塑造较行草书更难。
大字《阴符经》书写时间和《伊阙佛龛碑》大体相同或略早,在落款中有“起居郎”字样,褚遂良任起居郎在贞观10年,即636年,因而有此一说。《阴符经》笔势更加强烈,笔画间连绵牵丝呼应比比皆是。朱和羹《临池心解》说:“褚登善《阴符经》参以《急就》,以楷法行之,遂为千古绝作,其后无闻焉。”对照《阴符经》和《伊阙佛龛碑》,有很明显的差别,故有论者言《阴符经》的真实性要大打折扣。但伪作非劣作,米芾生前就极为推崇该帖,引以为范,受益匪浅。笔者认为,最重要的是《阴符经》可以体现出褚遂良的艺术水平,抑或是同时代学褚高手的模仿之作。《阴符经》除大字外,尚有小楷和草书两体,都是伪托之作。
最可信而又最能代表褚遂良水平的乃学王时期的代表作《雁塔圣教序》,作于653年,褚遂良时年58岁,已入暮年。原碑共有两块,在陕西省西安市大雁塔底层南墙,左右各一,至今保存完好。和学碑时期有明显变化,用笔藏锋逆入,一丝不苟,方圆兼施,笔画肥瘦互见,流利飞动,取弧势以增强笔力,参以二王行书笔法增加华美意蕴,相互间的动势呼应更加强烈,有意识地强调线条的曲线美和韵律美,风姿绰约动人。梁巘《评书帖》说:“褚书提笔空,运笔灵,瘦硬清挺,自是绝品。”结字中宫敛紧,疏密有致,字形宽绰,四周舒展,章法完全是汉隶格式,字间大于行间,气韵直逼钟王,而显褚家清逸。米友仁《跋〈雁塔圣教序〉》中说:“褚书在唐贤名士中为秀颖,得王羲之之法最多者。真字有隶法,自成一家,非诸人可比肩。” 可以说,《雁塔圣教序》是褚遂良个人书风确立的标志,用笔和结字都丰富多样,从方整向多种形式变化,融入二王笔意,摆脱欧虞面目,形成自我。当代书家潘伯鹰、徐无闻和沈觐寿等都是善褚书高手,皆以《雁塔圣教序》为范,足见影响之深。
褚遂良书法在唐代就产生了巨大影响。张怀瓘说:“薛稷书学褚公,尤尚绮丽媚好,肤肉得师之半矣,可谓河南之高足,甚为时所珍尚。”朱景玄《唐朝名画录》中称“薛稷学书师褚河南,时称‘买褚得薛,不失其节。’”对照薛稷书迹,虽名立列“初唐四家”,实际逊色。薛稷虽得其势,但失却了变化的随意和谐。薛稷从弟薛曜更胜一筹,对褚书不作亦步亦趋的模仿,而是加以发挥,有所创造。
薛稷兄弟之后,同年出生的张旭和李邕,则是褚遂良书风转变为颜真卿书风的过渡人物。唐代楷书也从初唐向盛唐逐步转型。张旭虽为一代草圣,但楷书功底惊人,风貌清虚简淡,仍然是初唐书风,受褚遂良影响很大。李邕楷书却大有改观。和褚遂良楷书一样,都为行楷。褚书中更多的保留了二王行书笔意和隶书痕迹,李邕不象褚遂良注重用笔的华丽巧饰,体现出碑格,笔画厚实,古拙刚硬,不乏婉转流畅,天趣自然,以“左低右高、上舒下敛”的结构变革二王行草,峻拔开张、稳固结实而气宇喧昂。李邕成熟期书法形态中很难找到二王的影子,用笔刚健,笔力雄强,无牵丝映带的虚笔连绕。通过横画欹斜来取势,这是李褚二人的共同点,但和褚书字形长宽扁高变化多相比,李邕字形变化要少一些,基本上忠实于二王体格。
颜真卿是唐代除薛稷外受褚遂良影响最大的书家。刘熙载《艺概•书概》中“褚河南之书为唐之广大教化主,颜平原得其筋”,从颜成熟期作品字形上来看,二者悬殊很大,实质上同声相息,颜从褚中化出,胜过薛稷仅得皮毛。颜字字形的宽博,捺画一波三折运笔,取法着意篆隶方面,都是受褚的启发。依笔者愚见,唐代精神暗合二王惟有褚颜二人。只是颜真卿将褚遂良的清逸变为沉雄,笔画细腻变成粗壮丰满,横画的欹侧变成从“平直到平直”,以正面示人,空间分割极为均匀,最大限度地发挥线条的张力作用,突破二王藩篱,洗尽贵族脂粉,以雄浑博大、黄钟大吕的盛唐之音取代了初唐潇洒飘逸的丰姿。在变法上,颜真卿比李邕更彻底。
宋代对褚理解最深的要数米芾,他在《续书评》中说“褚遂良如熟驭战马,举从动人,而别有一种娇色。”并且在《自叙帖》中说“余初学颜七八岁也,……乃慕褚而学最久。”米芾性格癫狂,自视甚高,在书学观念方面是离经叛道之人,籍助癫狂之口说出很多骇人听闻之语,诸如“一扫二王恶迹,照耀皇宋万古!”,“欧虞古法亡矣”,“颜书真入俗品”之类的话。但留心米芾言论,一生从未对褚遂良有半点微词。以米芾狂妄的为人,是不会轻易佩服一个人的,除非正对自己胃口。米芾对大字《阴符经》极为称道膺服,其行书用笔灵动多变,锋出八面,爽利有力,不能不归结于褚氏启发。
褚遂良一生书迹皆为行楷,因为他不愿耽于笔墨纸砚苦役劳顿,做个书工。他的成就可概括为两点,一是个人永无满足,不断探索,褚遂良实际上是由隋至唐楷书演绎的缩影,他一生墨迹的变化见证了这一点;二是他既能吸收前人精华,也能把握时代潮流,做到 “古不乖时,今不同弊”。褚遂良在习王浪潮下不能置身事外而另僻蹊径、独张一军,他的过人之处在于把握了书风变革的历史潮流,是二王体系中的得力干将,既实践了崇王理想
感觉褚遂良
薛元明
唐代楷书是后人无法企及的高峰,经历了初唐的奠定基础,颜真卿的集大成和柳公权的法度精整化等三个阶段。而初唐肇始“尚法”端倪,褚遂良功不可没,之所以这样说,因为褚遂良楷书和以往时代划上休止符,是唐楷第一人。在初唐欧、虞、褚三家书法中,虽皆承六朝遗风,融合南北不同风格,兼南北意蕴,但有明显差别。欧、虞入唐已是暮年,有“二王”基因,但更多北碑方正一路的影子,欧阳询表现的尤其充分和明显,清雅秀丽中包含雄强之气。虞世南书法较之“二王”风流潇洒而显得沉稳蕴藉,收敛了一些风流华彩。李煜说:“虞世南得右军之美韵,而失之俊迈。”而于褚遂良楷,则有很高的评价。《唐人书评》“褚遂良书,字里金生,行间玉润,法则温雅,美丽大方”。张怀 《书断》说:“褚遂良善书,真书甚得媚趣,若美人婵娟,似不任乎罗绮,增华绰约,甚有余态,欧、虞谢之。”
褚遂良书法风格明显地分为学碑和学王二个时期。学碑期宗欧、虞,受北碑书风影响,代表作有《伊阙佛龛碑》,此碑书于唐贞观十五年(公元641年),用笔工整,以方笔为主,结字方正平稳,以端庄取胜,极合法度,点画棱角分明,横画两头偏粗中间细瘦,略带波势,平正中见遒劲,捺笔一波三折,既有外拓之险劲,亦有内敛之含蓄,整体具浓厚的隶书笔意,揖让处理受汉隶《礼器碑》影响极大。苏轼《东坡集》中道出“褚河南书,清远萧散,微杂隶体”。这一时期代表作除《伊阙佛龛碑》外,还有《孟法师碑》,书写时间稍晚一些,变法已见端倪。行笔间有了起伏和较强的节奏韵律感,较之《伊阙佛龛碑》更为圆润秀媚,字型也开始有变化,左紧右舒。
学王时期主要代表作有《圣教序》,和前一时期又有明显变化,用笔藏锋逆入,一丝不苟,方圆兼施,笔画肥瘦互见,流利飞动,取弧势以增强笔力,参以“二王”行书笔法增加华美意蕴,相互间的动势呼应更加强烈,有意识地强调线条的曲线美和韵律美,风姿绰约动人。梁山献《评书帖》说:“褚书提笔空,运笔灵,瘦硬清挺,自是绝品。”结字中宫敛紧,疏密有致,字形宽绰,四周舒展,章法完全是汉隶格式,字间大于行间,气韵直逼钟王,而显褚家清逸。米友仁《跋雁塔圣教序》中说:“褚书在唐贤名士中为秀颖,得王羲之之法最多者。真字有隶法,自成一家,非诸人可比肩。”暮年之作《阴符经》笔势更加强烈,笔画间连绵牵丝呼应比比皆是。朱和羹《临池心解》说“褚登善《阴符经》参以《急就》,以楷法行之,遂为千古绝作,其后无闻焉。”
褚遂良书法在唐代就产生了巨大影响。薛稷是首位学褚遂良楷书之人。张怀 说:“薛稷书学褚公,尤尚绮丽媚好,肤肉得师之半矣,可谓河南之高足,甚为时所珍尚。”朱景玄《唐朝名画录》中称“薛稷学书师褚河南,时称‘买褚得薛,不失其节’”。对照薛稷书迹,虽名立为“初唐四家”,实际逊色。除薛稷外,唐代受褚遂良影响最大的当数颜真卿。刘熙载《艺概·书概》中说:“褚河南之书为唐之广大教化主,颜平原得其筋,徐季海之流得其肉。”从颜成熟期作品字形上来看,二者有很大悬殊,实质上精神暗合,胜过薛稷的单纯地走形式之路。颜字从字形的宽博,捺画的一波三折运笔,取法着意篆隶方面,都是受褚的启发,是从褚中化出的。依笔者愚见,唐代直通“二王”惟有褚颜二人。只是颜真卿将褚遂良的清逸变为沉雄,笔画细腻变成粗壮丰满,横画的奇支侧变成从“平直到平直”,以正面示人,空间分割极为均匀,最大限度地发挥线条的张力作用,突破“二王”的藩篱,洗尽贵族脂粉,以雄浑博大、黄钟大吕的盛唐之音取代了初唐潇洒飘逸的丰姿。
宋代对褚理解最深的要数米芾,他在《续书评》中说:“褚遂良知熟驭战马,举从动人,而别有一种娇色。”并且在《自叙帖》中说:“余初学颜七八岁也……乃慕褚而学最久。”米芾性格癫狂,自视甚高,在书学观念方面是离经叛道之人,藉助癫狂之口说出很多骇人听闻之语,诸如“一扫‘二王’恶迹,照耀皇宋万古”,“欧虞古法亡矣”,“颜书真入俗品”之类的话。但任何书家都是血肉丰满的,如果就这些来判定,不过是皮相之论。虽有偏颇,但是一家之言。留心米芾言论,一生从未对褚遂良有半点微词,以米芾狂妄的为人,是不会轻易佩服一个人的,除非正对自己的胃口。米芾对大字《阴符经》极为称道服膺,其行书用笔的灵动多变,锋从八面,爽利而有力,不能不归结于褚氏的启发。
褚遂良行书的隶意更多地保留在字形中,从这一点上来说,比起大王化为无形要略逊一筹,但正是这字形中的隶意,也就使后学者有了探寻的罅隙。褚遂良在习王浪潮下不能置身事外而另僻蹊径、独张一军,他的过人之处在于把握了书风变革的历史潮流,是“二王”体系中的一位得力干将,既实践了崇王理想,也构建了盛唐的法度,彻底完成了从尚韵到尚法书风的转变。朱长文《墨池篇》说:“遂良书多法,或学钟公之体,而古雅绝俗;或师逸少之法,而瘦硬有余。至于章草之间,婉美华丽,皆妙品之尤者也。”综观唐楷,欧、虞为北朝遗风,薛稷学褚而无个人面目,颜虽集大成,失之粗鲁,柳公权专尚清劲,但骨节嶙峋,寒俭之气时生,惟独褚遂良书浑厚华滋、丰姿绰约。“是褚遂良的字让人懂得什么是节奏,什么是书写的快感,什么叫得心应手。”(章祖安语)褚遂良对唐代书法乃至整个书法史来说,都是不可忽视的。
(编辑:佚名)
上一篇:从褚遂良说忠臣无下场 下一篇:谢权熠读有关褚遂良资料札记